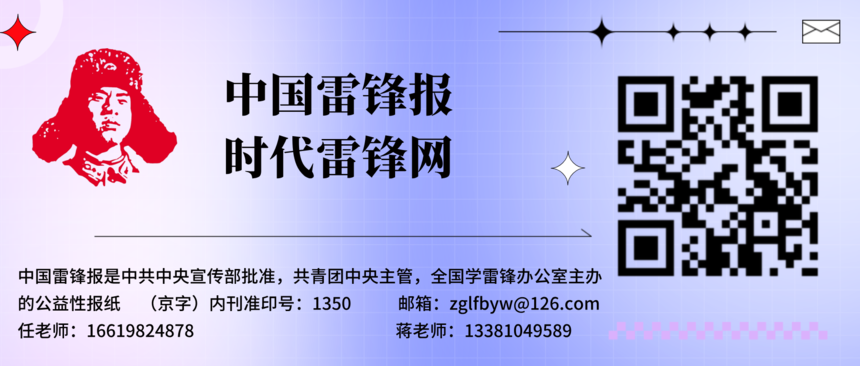|
铁骨铮铮八片存——九旬老兵李春祥的烽火长歌 中国雷锋报山东讯(邢以山 )光斜入窗棂,照亮了那张沟壑纵横的脸。97岁的李春祥抬起微颤的手,指尖在几处经年的伤疤上久久停留,仿佛仍能触到深埋的痛楚。“这里,一下打掉四颗牙,四颗门牙都没有了……”他喉头滚动,目光沉入岁月深处,“脑袋里还有八块铁片……大夫说,这辈子不能做核磁共振了。”
时光随着老人沙哑的讲述骤然倒转,回到1944年那个生死一线的春天。华北沦陷于日寇铁蹄,16岁的临清少年李春祥饿倒在尘土里,“走投无路啊,只能要饭,饿得只剩一口气。”濒死之际,一双有力的大手将他拽回人间——一位八路军政委救了他。这双手,不仅给了他活路,更将一条血火交织的抗日征途,铺展在这个瘦弱少年面前。 沉沉夜色成了少年初征的帷幕。“郭以当时在烟会取一法手一我们的任冬克尤是扒日本鬼子的火车道!”老人眼中倏然迸出火光。日寇的铁路是维系侵略的命脉,白天敌人驱赶劳工抢修,黑夜便成了战士的战场。“他白天修,我们就晚上扒!”斩钉截铁的话语如砸向铁轨的撬棍,铿锵作响,“破坏他的交通!这是最紧要的任务!” 战火中的日子,是钻防空洞、躲地道,在阴冷潮湿中屏息蛰伏。“白日蜷缩着,不敢高声语,不敢生烟火;黑夜便扑向那吞噬光明的铁轨——那是敌人输送物资与屠刀的血脉。”每一根撬起的道钉,每一段掀翻的钢轨,都如尖刀刺入侵略者的心脏。 枪林弹雨里,诀别与牺牲成了少年李春祥最深的烙印。“马新顺、王东孝、张玉华……”他念着三个同乡战友的名字,声音沉入水底。漫长的岁月之后,王东孝的名字终于在烈士陵园的石碑上觅得归宿,而马新顺与张玉华,却如沉入历史深海的石子,杳无音信。这成为他心头一道永不结痂的伤。 他摸索出一个珍藏的旧笔记本,里面厚厚一叠发黄的单据无声诉说。“给战友家属寄了四十多封信,始终没见到回信……”漫长的等待与无声的结局,是嵌入灵魂的遗憾。 “打仗时害怕吗?”面对提问,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兵回答得没有丝毫犹豫:“不害怕!要为战友报仇!”声音陡然拔高,带着倔强的千钧之力。那“不害怕”三个字,是无数个黑夜面对炮火与死亡淬炼出的钢铁;那“报仇”的誓言,是支撑他从血泊中一次次爬起冲锋的脊梁。
1949年6月,带着满身伤痕与硝烟记忆,李春祥解甲归田。战火停息,英雄并未远离乡土。1950年,这位枪林弹雨中闯出的汉子,又默默挑起临清市姜油坊村党支部书记的重担。和平的土地上,他俯身耕耘,如同当年守护疆土。 然而战争的馈赠——那八块深嵌血肉的铁片,成了他无法摆脱的勋章与枷锁。它们时时提醒着过往,也阻挡了现代医学的探照——他终身与核磁共振无缘。 2022年初春,刘垓子镇发起“党员一盏灯,企业一份情”捐款活动。93岁的李春祥执意亲自赶到现场,将省吃俭用的500元钱郑重塞进红色捐款箱。“我岁数大了,能帮到村里的不多,就献一点爱心吧。”村支书姜金鲁感慨:“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!” 他更以另一种方式燃烧着生命余热——成为十里八乡闻名的“红色火种”。在党支部的夜会、在乡村小学的课堂、在喧闹的集市,这位九旬“老革命”走到哪里,就把血染的记忆讲到哪里。 在姜油坊小学,佩戴上红领巾的李春祥对孩子们讲述锦州战役的严寒:“零下二十多度,走了七天七夜,没棉衣,没人喊冷……”讲到平津战役,他声音微颤:“一枚炮弹落下来,两名战友当场牺牲,弹片打中了我……”他反复擦拭着珍藏的退伍证,目光悠远:“现在的日子可太好了,可惜很多战友都看不到了。” 少先队员代表郑重承诺:“李爷爷,我们一定做新时代的合格接班人!”老人欣慰而笃定:“我虽然老了,但要培养好接班人,把党的事业传下去!” 阳光再次落在他沧桑的面庞,那八块深藏颅内的弹片,如同历史在血肉中铸就的印章。它们沉默地见证着:从濒死乞儿到烽火战士,从战场英雄到乡野烛光,一个用铁骨与赤诚贯穿的生命,如何将个人的命运,深深锲入民族救亡与复兴的壮阔史诗。这铁片是伤疤,是勋章,更是一颗在和平年代依然滚烫、依然搏动的不朽红心——它属于李春祥,更属于一个从血火中挺立的不屈民族。 审核:王凤军 值班:任安广
|